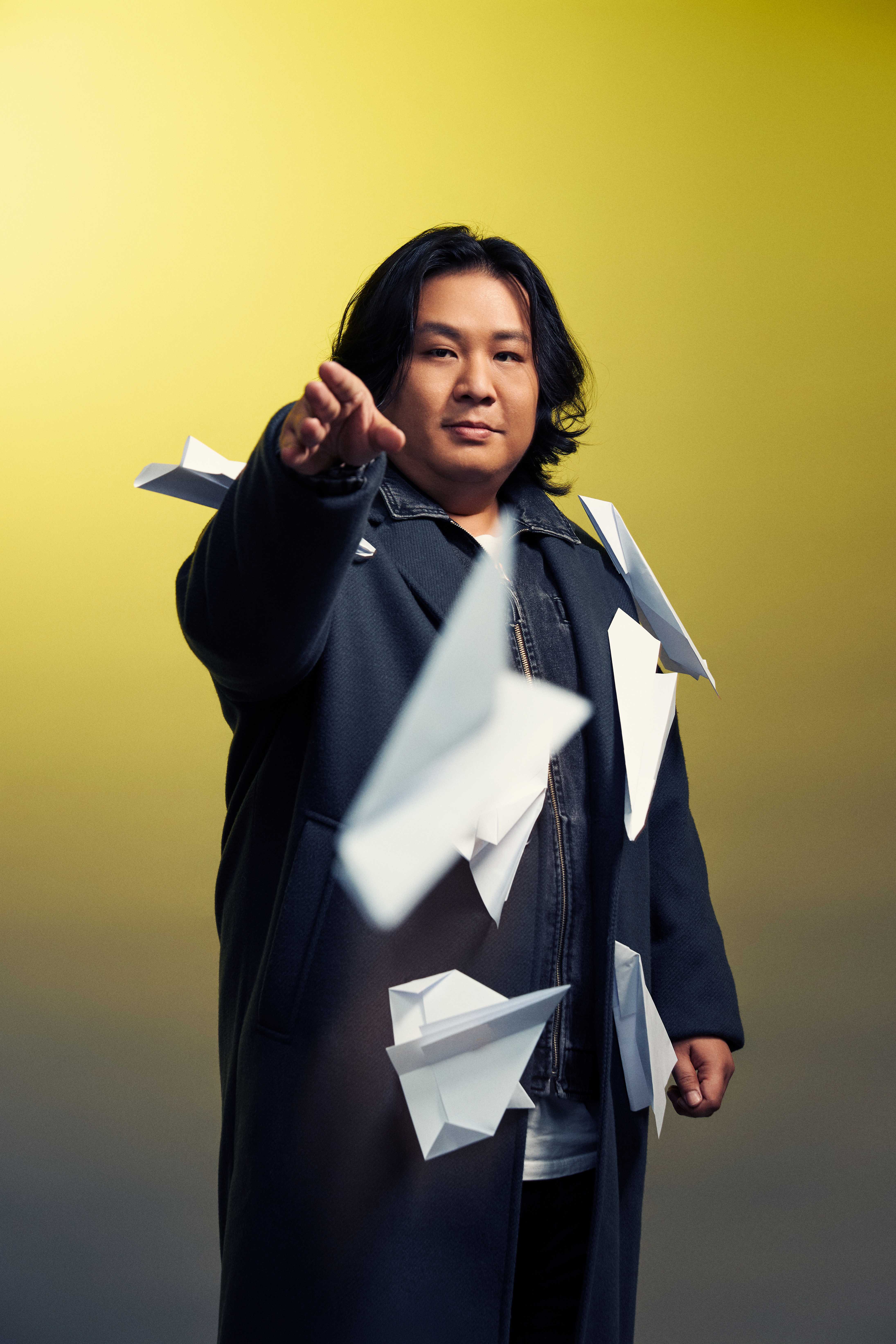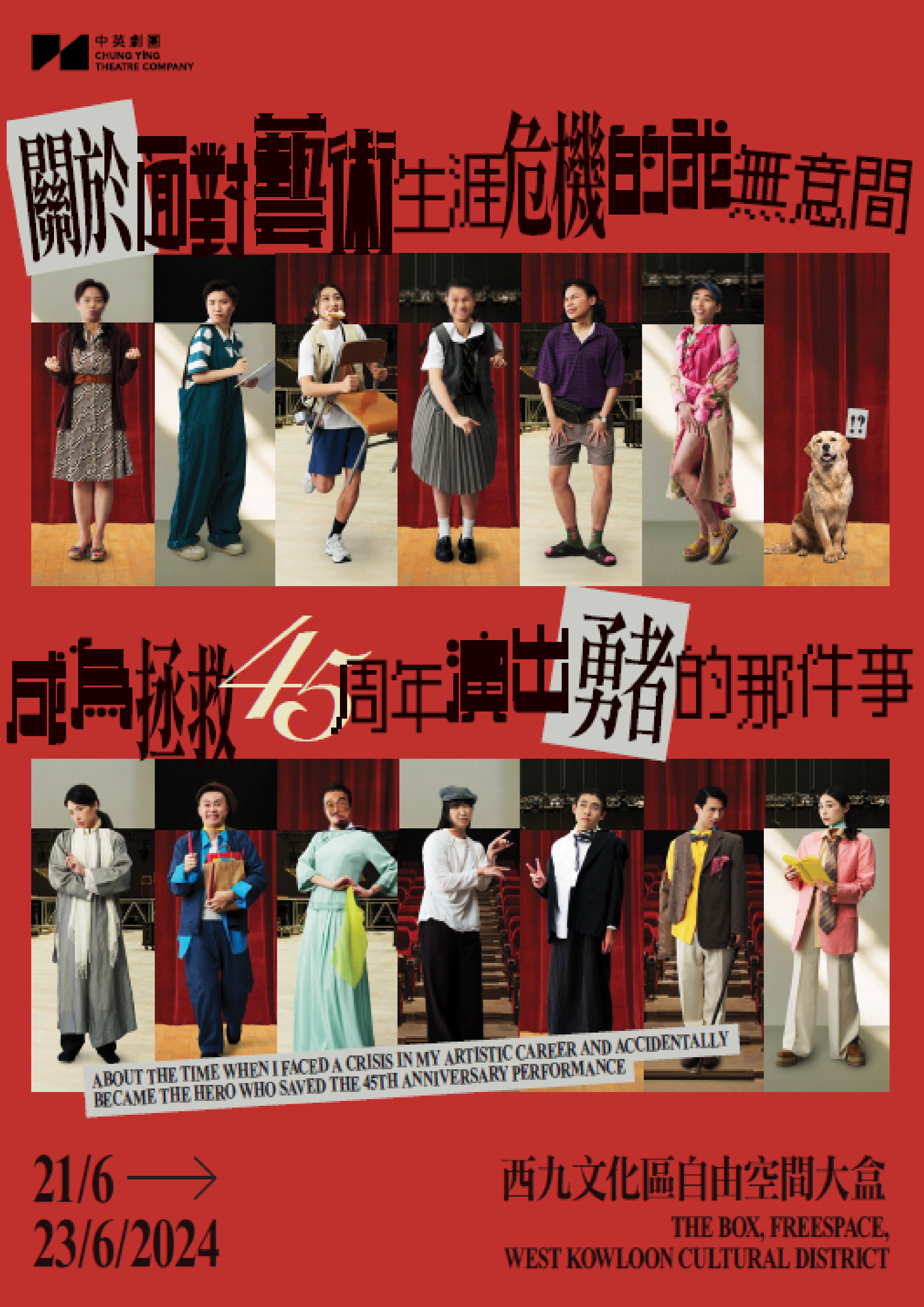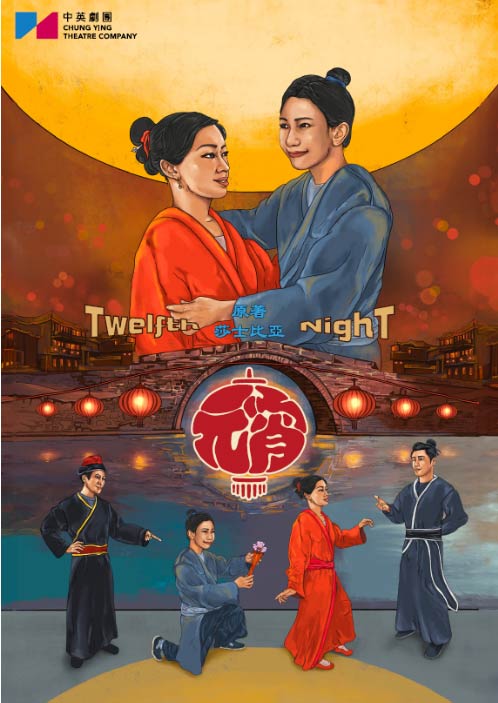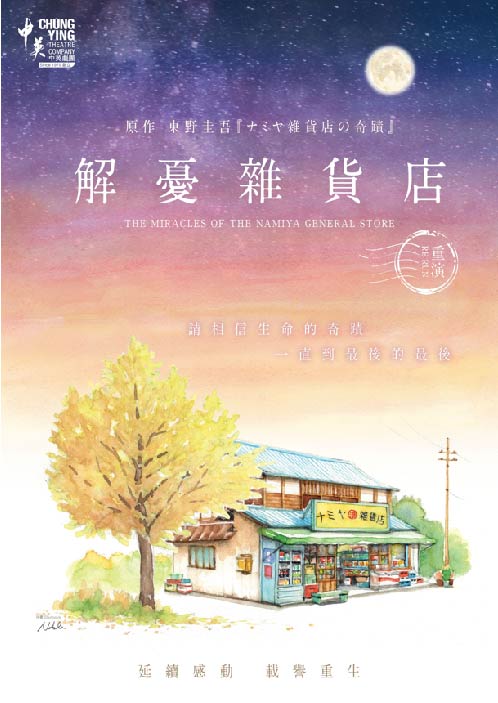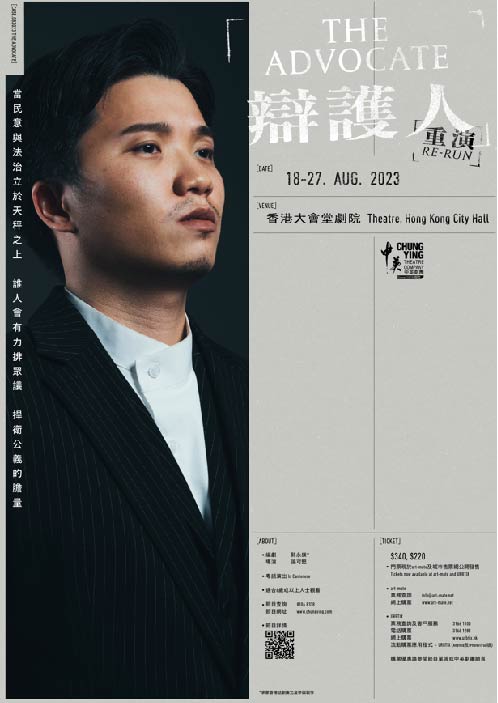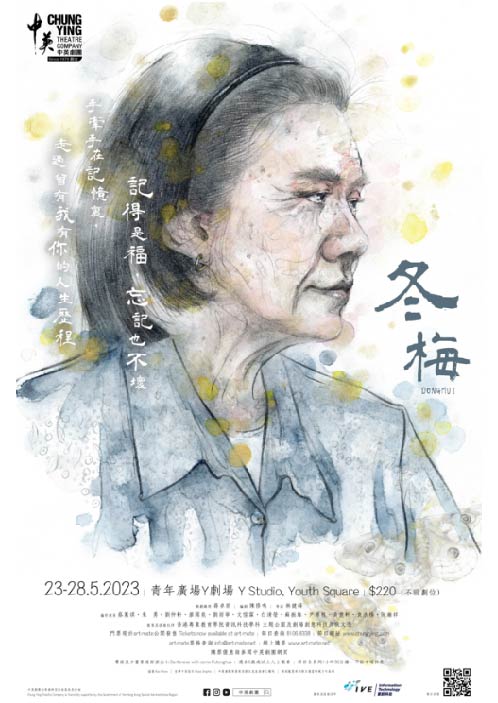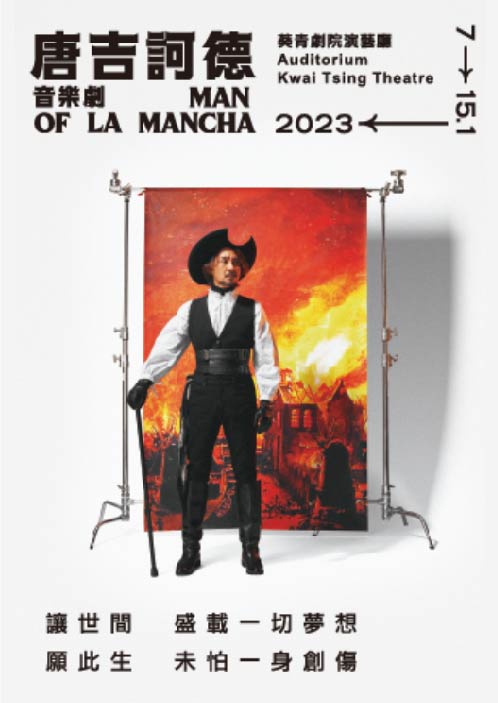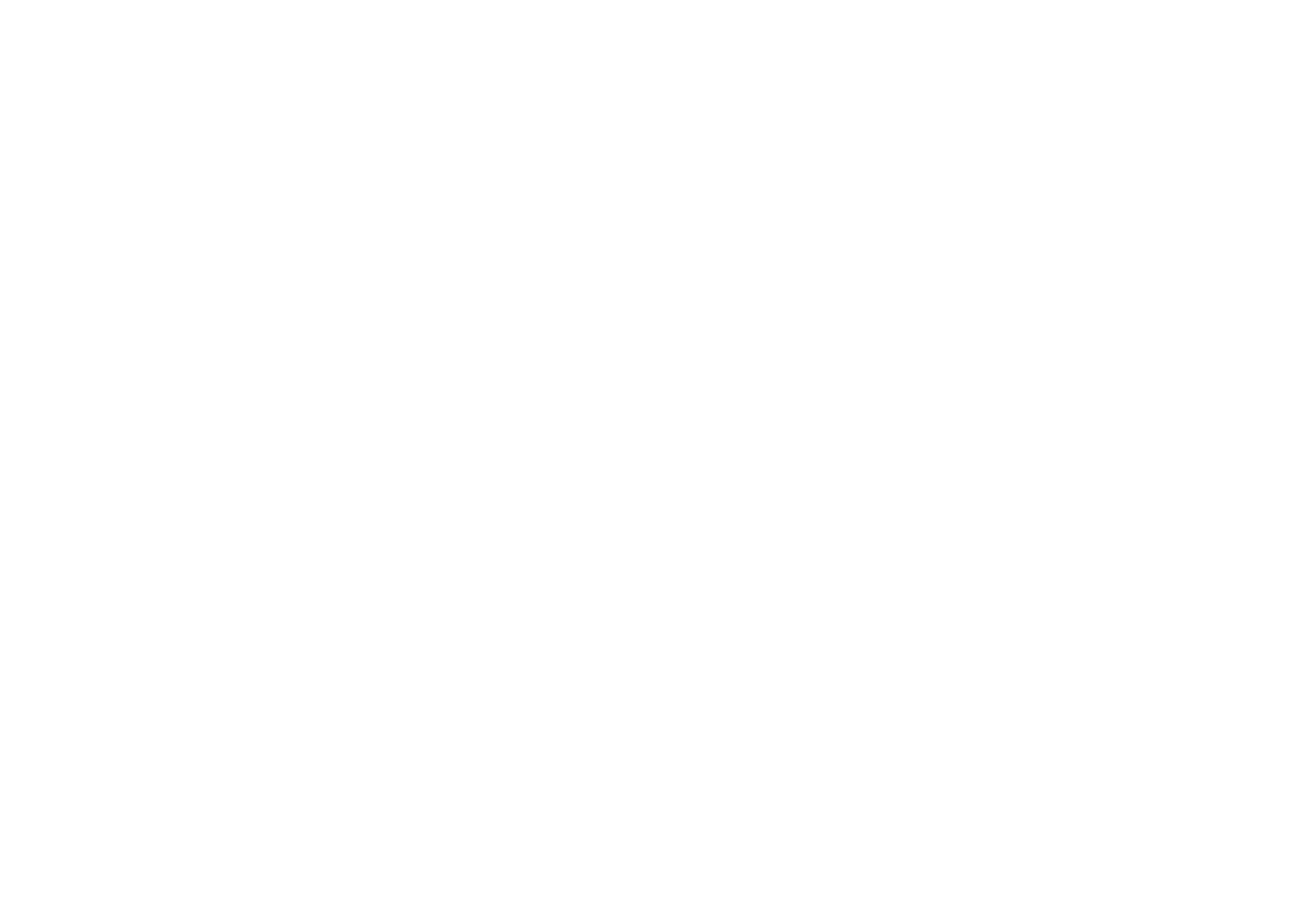如果我們生命不苦
在劇場要放下「這是我的作品」這個想法。人越大越明白一個演出的生命力並非來自創作者的思路,而是表演者的汗水。團體遊戲不應只有一個人開心,世界也可以有不只一種正確;我該建立一個戲劇世界刺激演員創作,而非想像一個終點逼所有人前行。
有種執念叫作「被喜歡/被認同」,它最常見亦最不易被察覺,因為它很少引起強大的反作用力。它就似溫水煮蛙,慢慢將人的目標、鬥志、執着煮死,煮剩媚俗與惰性。然而最引人入勝的角色,往往有着異於常人的執念;這大抵也是人生總是苦的原因——但如果生命不苦,藝術意義何在?之於藝術創作,執念更應當被重視。因此,放下是佛家的事,而不是藝術家的事。正因放不下,人的每一個情感都令我動容。掙扎是最美好的狀態,熱忱是受難的開始,烏托邦始終只存在理想之中,想與觀眾同行,就別脫離苦海。
去成為觀眾,去與同路人相遇,在另一時空同步掙扎呼吸,這種溫度未必最暖心,卻很熾熱、富生命力。看化可能只是一種絕望,就算失望,不能絕望。假如美狄亞看化人性的真相,接受丈夫的惡,只會出現在佛經中而非劇本中。然而美狄亞一刻間母愛與仇恨的拉扯,卻讓這種痛化為永恆,數千年歷久常新,仍與今日的靈魂共鳴。
我想,這便是戲劇的核心吧。